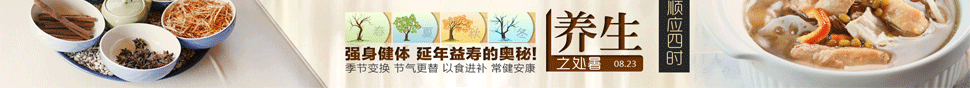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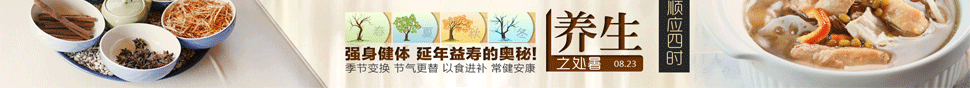
也许大家对“过河”问题再熟悉不过了,那么也请允许我不厌其烦的再累述一下这一问题。
问题:一个摆渡人,要把一条狼,一只羊,和一捆草从河的西岸运到河的东岸,因为船小,除摆渡人外,一次只能运一个“乘客”。显然,摆渡人不能让狼、羊单独留在岸边,也不能让羊、草单独留在岸边,问怎样才能顺利过河?
相信大多数人在读完题目后,并没有对出题者有任何非难,而是“乖乖地”开始解题。
第一种方案:
第一次:将狼、羊留在西岸,人、羊渡到东岸,然后人返回,留下羊;
第二次:人、狼渡到东岸,然后人、羊返回,留下狼;
第三次:人带着草渡到东岸,人回来,留下狼、草;
第四次:人、羊渡到东岸,顺利过河。
第二种方案:
第一次:同方案一;
第二次:人带着草渡到东岸,人羊返回,留下草;
第三次:人、狼渡到东岸,人返回,留下狼、草;
第四次:同方案一。
此刻大家似乎就完事大吉,可以享受一下成功者的喜悦了。可有没有想过,在题目的设置上,我们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提示的前提下,就默认了狼、羊独处,羊就将被狼吃掉;羊、草独处,羊就会吃草呢?而没有想过对人有一定攻击性的狼会吃人,“东郭先生”不就是“过来人”吗?而且“狼来了”的故事大家也耳熟能详啊。
现代社会,人什么都可以吃,昆虫、花、猫、猴子、蛇……吃草亦有可能,人吃狼,狼吃人,相互作用吗,所以这道题也应有所发展,该加上一些严谨的假设:人不能活吃狼、羊,但在茹毛饮血年代可以,现在却不行,煮熟了还成;人不吃草,草不吃人(可以省略,因为是“一捆草”。
目前在科学研究领域,无生命的植物尚不能食肉,这里的草和食虫草,食人树等有生命的植物不可比);大多数情况下,狼不吃草,因为实际上狼个别季节也吃草,狼得能吃羊,似乎要有一个假设,一只“软弱的”羊,和一条“凶狠的”狼,因为“狼爱上羊啊,爱得疯狂”,那可就出问题了,动物园里的狼多数也不吃羊,因为野性尽失,由“性本恶”转变为“性本善”了,成为“温和派”了,但吃羊肉,再加上假设狼不能吃人;羊不吃狼、人,似乎没什么问题,但得吃草,因为现在饲养的羊已经不怎么吃草了。
那么,在满足上述假设条件后,这道题似乎有些可怕,可以称得上“世界难题”,怎么解?或者说根本无法解。
那么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题!
问题就应这样叙述:
在不发生任何天灾、人祸、兽祸、畜祸及UFO事件的前提下,一个摆渡人(正常人,不吃狼、羊、草),要把一条狼(“纯”野性且规定不吃人、草),一只羊(温顺的羊,不吃人、狼,但得吃草),和一捆草(现实的草,没有任何神话色彩),从河(没有“河神”,不发生任何意外,保证本题顺利进行)的西岸运到河的东岸,因为船小(结实,确保在本题的求解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故障),除摆渡人外,一次只能运一个“乘客”,显然,摆渡人不能让狼、羊单独留在岸边,也不能让羊、草单独留在岸边,问怎样才能顺利过河?
这样问题就可解啦!
正如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样,我并不是钻“牛角尖”,初衷也正是通过这些来使更多的读者冲出那种“逆来顺受”的思维模式。创新、批判才能有所发展吗,而对一道题,固守陈规,就如同认为“名人”画的画叫“名画”,“名人”写的文章叫“名篇”,“名人”的名字叫名字一样,噢,还是名字啊,算我没说。做一切事情都要严谨,类似说话要谨言,做事要慎行,像“明星”们学习,因为一不小心,就可能成为“头版头条”,街头巷议的谈资。
当然本题的一些假设可能会让某些人嗤之以鼻,或让某些人开怀大笑,但都无妨,交流嘛,并不是很严肃的问题,只是采用比较有亲和力的叙述形式而已。
最后与大家分享一段比较精彩的对白吧。
#深度好文计划#一位文学家看到一位数学家在写《论小说与散文之间的关系》。
文学家说:“你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怎么研究起文学来了,怎么可以涉足人文科学呢?你有‘基础’吗?”
数学家说:“我是研究我们的文学,而不是文学家的文学。”


